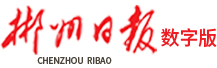参赛作者:陶琳(嘉禾县龙潭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窗外的山茶花第三次落在镇政府大院时,青砖墙缝里已蓄满三年的光阴。来到郴州之后,总觉得湘南的春色比别处更迷人些,檐角滴滴答答的雨珠裹着春天的问候,宁静而温润。相比于城市里的风云变幻,乡野的云雾仿佛走得更慢,所以云里的雨也下得悠悠长长,连同地上的人、手里的物、心中的念头也是悠悠长长,它们游走在宗祠的雕花门窗间,游走在青青嫩嫩的菜芽尖上,游走在垄上月牙白的青烟里。
在毕业之前,我对于乡村知之甚少。在城市中被“圈养”的时间一长,总有一种机械化的木讷感,生活也非常程式化。如今当我真正面对一项可以称之为“事业”的工作,以及我在这里的成长,可以说无愧于青春。满坡山茶花在暮色中浮沉如雪,让我头一回知晓山岚是有重量的——从龙脊般的褶皱里漫出来,浸透青瓦白墙。
试试召集“一些”年轻人
霜降那日收到朋友从浙江寄来的包裹,拆开是半截老屋梁木雕成的镇纸。视频里她正带着美院学生在夯土墙上作画,残垣断壁间绽放的无限创意,让我的保温杯里突然泛起咖啡般的苦涩。体制内的齿轮自有其运转的规律,但那些深夜伏案的时刻,灯光会在玻璃窗上投下两个影子:一个伏案写材料的选调生,一个在想象中培植乡村艺术的造梦者。
在手机屏幕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划拉那些“乡创”活动的剪影,细细品味这种富有创造力的模式,他们会抛出一个课题,招募一些在校生、青年创业者、青年艺术家等人群,让他们来为乡村运营出谋划策。主办方为青年提供基本的食宿,青年以志愿者的身份为当地乡村留下作品。这样一种交互的模式,一方面,给青年带来独特的体验;另一方面,为乡村聚集了人气。即便只是短暂的停留,如果足够有吸引力,经过大浪淘沙,也可以留下真正可以从事“乡创”工作的人。
去哪里找第一批年轻人?
找年轻人到村里来很难,难就难在如何与青年建立信任,让他们相信这样一场旅途是意义非凡的。如果贸然去发出这样的招募,必然是石沉大海的结果。
我想,或许可以从“自己人”找突破口。
冬至过后的一天,我拨通了L师妹的电话,她正在新加坡参加一场中文和书法交流活动。她身后游走着书法研习班的各国青年,墨迹未干的“龍”字在宣纸上舒展爪牙。“师姐你看,他们连‘永字八法’都不熟,却敢用丙烯在帆布鞋上写《离骚》。”她突然把镜头转向自己,“我见过你照片中的湘南乡村,相信大家会像我一样很感兴趣的!”
报名表如春笋般在邮箱里冒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涌起阵阵感动。面对相隔几千公里的一个陌生乡村,他们在未知全貌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相信我。一场两个月后的实践活动就这样一拍即合。
我想我一定不能叫他们失望。翻箱倒柜在铁皮柜里找到之前去文化馆时馆长给我的一张嘉禾县非遗名录,泛黄的旧页突然有了一些温度。
收集散落的文化,一时间成了我的首要任务。
“龙就是人”
我开始重新梳理所在乡镇的文化。这个乡镇叫龙潭镇,平时百姓的文娱活动很有限,但是节庆期间总不乏舞龙队的身影,或许以“龙”为切入口,会有一些收获。
我先是询问了一些村党支部书记,他们又带我去问了一些上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这样层层向上溯源。对于龙文化在本乡镇的起源,他们能谈的内容不多,不过舞龙确实有很多风俗上的讲究,譬如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龙脉”,不同的村有可能是“单龙脉”或者“双龙脉”,跟本村的历史地理有关。
“扶塘村花园头有一位老人,做龙头做了几十年,你可以去问问他。”
“扶塘村?他叫什么名字呢?”扶塘村是我所驻的村,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手艺人。
“具体不清楚,反正我们在他那里买龙。”
扶塘村
大寒时节,在扶塘村口遇见卖糍粑的妇人,她竹匾里的米团子个个白白嫩嫩,好不诱人。“老辈人说‘龙脉’就是人脉呢。”她笑着指向远山,“这就是我们的后龙山,人人都说我们这里的‘龙脉’旺!”
原来,“龙的传人”不是一句虚话。
三年前来到乡镇的第一天,我就跟随书记拜访了这个村。还记得那是一个炎炎夏日,驱车一进村口,荷叶翠绿满目,令人难以忘怀。后来每一个从村里下班的傍晚,这片荷田都能给我带来治愈。在晚风中驾驶离开,我会播放一首Coldplay的《Amazing day》:
…………
Can the birds in poetry chime
Can there be breaks in the chaos sometimes
…………
“诗中的鸟儿能否歌唱”,我不得而知,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整个村庄都在跟我对话。
2020年,村里面第一次试着流转了10亩土地给大户养殖荷花,到2022年已经扩展到100多亩的面积,就是我眼前看到的这一片。村里为提高产品附加值建了莲子加工厂,但是一年的效益也还是有限,主要是规模仍然微不足道,无法形成产业型规模。即便如此,这里的荷花也能吸引慕名而来的游客,夏天总是有扛着摄像机的人络绎不绝来到这里。
扶塘村是一个“龙脉很旺”的地方,因为这里绵延不绝走出去了很多人才,更不乏回来建设家乡的游子。除了荷花以外,在远处的周家洞水库大坝上,还坐落着一个花海生态园。花海之为花海,是有着800亩的樱花,早春寒冷还未退却之际,它们就会悄悄布满整座山丘。与冬梅的清冽相比,它们更多地带着一丝温存。
“过去常常有人在我这里买龙”
去到曹爷爷家的时候,天气还很冷。村党支部书记带我走到花园头自然村议事大堂附近时,我惊呼:“这不是7月份走访困难党员的那一户吗?”
“是啊,就是这个老人家。”
曹爷爷出来迎接我,招呼我到里屋烤火。他总是亲切地唤我“小孙女”,因为我跟他的三个孙儿差不多大。他儿子去世得早,留下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由他和老伴儿抚养,虽然很辛苦,但是现在三个小孩都已长大成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大学。
曹爷爷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做过记者,也当过村委会主任,有知识有文化,口才也很不错。回想起建党节那天曹爷爷给我们上的一堂党课,言犹在耳。当时也是围坐在这张烤火桌边,曹爷爷讲道:“我们的父辈很苦很苦才把我们养大,就是要我们去报效祖国和人民。你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要珍惜党和国家对你们的信任,廉洁奉公、执政为民。”
我问:“您还会编做龙头吗?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起过?”“做龙都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过去常常有人在我这里买龙,但是现在没有人买了,自然也就不做了。”他难为情地回答。
虽然这段叙述多少令人惋惜,但是今天找到曹爷爷的这门手艺已经是意外之喜。曹爷爷从二楼拿了几个老旧的龙头下来,告诉我做龙头的大概步骤,从搭架子、破篾、找龙棍到打孔、做骨架、蒙纸、上色、抛光,每一步都不轻易。我看到被岁月蒙上灰层的一排龙头,它们纹路各异,造型不同,可那一双双眼睛却都有着鲜活的张力,仿佛诉说着过去的一切。
曹爷爷演示扎龙头那日,火炉里煨着偷藏的往事。篾条在他指间化作游龙,他跟我说做“龙”是很看机遇的,有的时候会做出一条“严肃”的龙,而有的时候可以做出一条“古灵精怪”的龙,全凭他个人发挥。当时正值寒假,他的三个孙儿也在一旁细细听讲,只是面对我们还都是怯生生地躲在爷爷奶奶背后。
我向曹爷爷说明了我想请一批大学生到村里来学习做龙的想法,他一开始很惊讶,仿佛用眼神问我这个手艺值得被如此放大吗?我只是给他一个坚毅的眼神作回答。在我看来,这些才是乡村的根本,是不能丢的。
“爷爷您现在还有时间做龙吗?”
我比较担心的是曹爷爷现在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配合我完成这样一场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毕竟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家里也有很多事情要忙活。可是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我,说:“现在又没有人来买龙了,要是你不来问我,这门手艺就烂在肚子里了!”
“欢迎你们!”
我很难忘记那样一个下午,在这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欢声笑语、掌声雷动。
“感谢你们这些小燕子,飞到我的家乡,送知识、送文化、送智慧、送胆量、送繁荣昌盛,欢迎你们!”曹爷爷的课讲得生动有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仿佛不仅是在听做龙头的古老技艺,更是听老一辈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动手环节,同学们分成了几组,有的在和竹架子“较劲”,把它们弯成想要的形状,直感叹就算有力气也拧不成一个想要的龙嘴;有的把蚕丝糊在竹架表面,用牛皮水不厌其烦地加固,直到蚕丝成为一张厚实的纸面;有的竭尽自己的艺术天赋,把校徽画在已经糊好的龙头上。
爷爷的三个孙儿也自信地当起了“老师”,把他们跟爷爷学来的手艺告诉同学们。我则穿梭在他们之间,沉浸式地感受着龙头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匠心。文化传承的意义,大概就是这样连接一代又一代人,也连接着不同远方的人们。
元宵节
正月十五,是同学们行程安排的最后一天。
我邀请他们留下来和乡亲们一起闹元宵。虽然时间紧张,我们也想用团队的力量策划一场群众文化活动。我叫上了镇里的年轻人,大家做方案的做方案,排节目的排节目,和村民对接的对接。舞龙、花灯戏、伴嫁歌、抖糍粑,乡亲们热情很高,有的连夜去买了崭新的戏服,有一种拿出看家本领的气势;有的立马嗅到了商机,在家里做了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等着节日当天摆摊贩卖。同学们这边呢,也想着出一个节目,为大家合唱一首《龙的传人》,不失为一个点题的想法,他们戴上了自己做的龙头,排成龙形状的队伍。
元宵节那天天朗气清,小小的广场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大家虽然只准备了一两天,却也给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村民们唱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花灯戏的内容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们绽放的笑脸上,我看到了乡村最具魅力的一面。
青年桥梁
八百年前,周敦颐在郴州著《太极图说》,架起儒道思想的融合之桥。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城乡交互从来没有像这样迫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搭建一座桥梁,当每个青年成为一块有温度的桥砖,我们终将连缀成跨越山海、通向未来的潇湘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