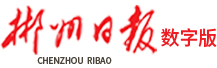□ 郭垂辉
萧育轩离开人世间已有13个春秋,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与其文学作品一样,被定格在南岭大地上,激起历史的回响。我们追忆萧育轩与郴州文学崛起的世纪之缘,更多的是记录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为郴州文学新生代作家创作与成长提供参考和借鉴。
萧育轩的文学启蒙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二,萧育轩出生在当时的安化县丰乐乡檀山村一个泥水匠家庭,在七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五,在男丁中排行老二。老先生给家中男孩以“钟灵毓秀”名第之,他应名毓灵,但发现“灵”字偏女性化,于是老先生灵机一动,把“灵”字改为“辉”。萧育轩自己粗识文墨后,觉得“毓辉”二字繁杂,便简化为“育轩”。
萧育轩本是新学发蒙的。因别人撺掇,说新学出不了“秀才”,父母便执意让他转到一家私塾,跟《幼学琼林》《孟子》打交道,虽然满肚子塞饱“子曰”“诗云”,但临到上高小时,他和父母都傻了眼,因为新学要考语文、算术。于是,母亲抱着一只老母鸡,拉着他去找一位远房舅舅求情。父亲也没闲着,恳求他的东家出面斡旋。新生考试发榜时,他居然名列前茅,原来,是一篇作文打动了老师的心。这所学校叫“观澜小学”,因门前湄江急滩而得名。
高小毕业后,家里的顶梁柱——父亲撒手去了天国,萧育轩面临失学。好在“劝学运动”来到村里,可怜的母亲拗不过那些老师和学生妹子的甜言蜜语,咬着牙把他送进了桥头河建国中学(今涟源市第四中学)。他读通学,来回10公里,天亮出门,黄昏归家,到了冬季往往两头摸黑。雨雪天,一双草鞋,冻得上牙和下齿咬得咯嘣响。最难熬的是中午没饭吃,别人吃中饭和午休时,他就在学校图书室埋头看书。初中期间,他读完学校图书室的大部分文学书籍,开始接触西方文学。
初中毕业后,家里实在无力供他上高中。母亲含着眼泪说:“伢子,你自寻出路吧,我这把老骨头再也熬不出油。”于是,萧育轩报考了不用交学费又能很快挣到钱的学校。皇天不负有心人,萧育轩居然考上了沈阳电力技工学校。毕业后,在学校的关照下,他回到湖南,被分配到郴州正在兴建中的鲤鱼江电厂,当一名锅炉工。
萧育轩从小痴迷文学,立志要当作家。他说,这与家乡的文化氛围有关,与其用“钟灵毓秀”四字来取名,还不如用来描述家乡的秀丽风景:前有蒋家、中州二段,一眼平川,清澈的归水从二段之中蜿蜒流过,给庄稼带来勃勃生机,是百姓的米粮仓;后面是青翠的山峦,古木参天,飞禽走兽,一条古驿道,青石铺成,从安化盘旋而来,打自家屋门前经过,贩夫走卒,络绎不绝。一年四季,百花竞放,檀木飘香,好一幅桃花源似的画卷!难怪蜀国第二任宰相蒋琬要在这里建立庄园。村子取名檀山,名不虚传。
萧育轩说,他的文学启蒙,还“搭帮”村里的三个“贵人”:一个是视力障碍者,一个是肢体障碍者,还有一个是篾匠。视力障碍者是八字先生,走村串户,给他带回数不清的见闻和故事;肢体障碍者是视力障碍者的弟弟,是专治无名肿毒的江湖郎中,萧育轩给他打酒、买盐,郎中就教他唐诗和封血的“神咒”;篾匠住在上边屋,放工回来,萧育轩也夹在大人中间,一边围炉取暖,一边听篾匠口沫横飞地讲《粉妆楼》。后来上私塾,老先生到了放晚学前,照例一边呷酒,一边给萧育轩讲《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为萧育轩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萧育轩说,进了工厂后。因自己生性笨拙与孤僻,又与唱歌跳舞绝缘,业余时间就只有抱着小说“亲热”,把厂里图书室的文学书籍看完了,自己还从可怜的工资中节省钱来购买书刊。他看多了小说,觉得作家不过如此,自己也能写得出。于是,他写起小说来,开始怕别人打小报告说自己不务正业,有成家成名的资产阶级“臭思想”,所以只能躲着写,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萧育轩的短篇小说多次震惊湖湘文坛
第一次:《刘兰》
《刘兰》写于1962年5月,约8000字。萧育轩在小说中写道:老实朴素的刘兰,接手电厂仓库保管员的工作后,全神贯注地做好车间班组生产物资器材的科学管理和分发。为扭转前任管理不善、器材发放随意造成的不良后果,她坚持原则,哪怕对自己的爱人也是铁面无私,按车间班组的业务需求,严格把关,杜绝了有的因多领冒领器材积压浪费、有的又因领不到器材生产受阻的怪事,塑造了一个棱角分明、性格鲜明、具有工人阶级宝贵品质的青年女工形象。
小说于1962年8月发表在《湖南文学》头条位置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和反响;被译成英文在《中国文学》上转载,改编成花鼓戏,出版了连环画;1963年入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编辑的《工人短篇小说选》。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刚回湖南省文联任职的著名作家康濯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到这篇小说,说刘兰姑娘漂亮可爱,乐观清朗,头上长角,嘴里含蜜……充分肯定了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这是萧育轩的处女作。28年后,萧育轩写的散文《寻找刘兰》,讲述了他当锅炉工的这段经历。有一次,锅炉班班长给他组里领来了七个学徒,放眼一看,有三个是女的,组里原来是男人的世界,大家都愣住了。他也感到好为难,男性学徒很快被师傅们领走了,留下三位女性,可怜兮兮地眨巴着眼睛。三位女学徒,小彭19岁,小余17岁,小张16岁。萧育轩寻思,组里还有其他几位师傅,没有他“一带三”的道理。于是,他第一次施行了组长的权威,说,为公平起见,他带年纪最小的小张,把小彭、小余指定给另外两位师傅带。被组长强制带女学徒的师傅却说:“挂我们的名可以,做事学技术嘛,还是劳组长大驾吧。”一声哈哈,屁股一拍,乐呵呵地走了。
萧育轩苦笑着,心想这下可好啦,不仅要当师傅,还要做娘了,而自己,才二十出头哩。
可正是这段费心带学徒的操劳,丰富了他的生活,让他获取了创作的源泉。处女作篇名《刘兰》,是根据小说中主人公的芳名取的,刘兰的原型就是三个女学徒。文中有些生活场景,甚至有些语言,都是原样地搬到纸上的。
萧育轩说,我不能忘记《刘兰》。她沉重得像十八磅榔头,帮助我砸开了文学殿堂那难得敞开的大门。同时,情随马鞍,伴我走过了厄运连连的文学四十年。
其实,在写《刘兰》这篇小说之前,萧育轩曾写过两篇小说,投寄出去了,几周后就收到原稿和打印有几行字的退稿信。他不甘心,事不过三,决心再写一篇试试。于是,用汗水泡制出了《刘兰》,选定投《湖南文学》,苦盼苦熬十几天后,终于等到回信,当沾满油灰的黢黑的手接到那叠厚厚的回信时,似乎也预料到没有好运。他拆开信封瞄了一眼,果然没有变成铅字,还是原样折叠起来的原稿。中午,他回到宿舍,喝了二两酒,即火爆地决定:改换门庭投邮。就在他取出原稿抖动稿子时,连退稿信也没有看到,稿纸上的烟灰和红墨水却令他激恼,于是带着怒气翻动原稿。烟灰、红墨水、几个简短的眉批。到最后一页,剩有半张空白,填满酒杯粗的红笔字:
此稿题材和构思尚可,只有几处(我已在稿子上标明),请加以修改。发表时,建议用真名,不必用近乎外国人的名字。
萧育轩当时的感觉是,这位编辑懒得或许架子大得吓人;开头没有写作者的名字,结尾处更没有署上自己的大名。
《刘兰》发表后不久,这位编辑来到鲤鱼江。他大名叫李青,是当时刊物分管郴州地区业余作者稿件的责任编辑。从省城下来,他除了要见萧育轩,还要见前几个月在《湖南文学》发表了处女作的古华。那时的李青四十岁上下,颀长的身材,英俊的脸孔,穿戴整齐,风度翩翩。略显微胖的萧育轩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刚从锅炉房出来,脸上还有黑灰,一双塑料凉鞋也有自己用锯片烙补的疤痕。而古华也刚从地里奔来,一双失去了原色的解放鞋沾着黄土,鞋面边缘帆布都有撕痕。那时古华年方二十,萧育轩比古华大五岁。三位不同身份的人首次相见,各自都十分高兴。特别是萧育轩和古华都惊呆了:啊,没想到我们是隔壁邻居!
李青本想做东请两位作者吃饭,可是苦日子刚刚过去,附近没有馆子,而热心的萧育轩坚持肚子问题该他做东,于是,在食堂选了最好的菜打了几钵子,在宿舍里摆开书桌,三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李青和古华都不喝酒,但他俩被萧育轩逼着抿了几口。
席间,萧育轩发现这位编辑,谨言慎笑,但很随和,学识渊博,懂得很多关于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知识。送走李青后,萧育轩对古华说:“这老师我信得过,跟他学艺,不怕上不了《人民文学》。”
一位编辑和两位作者三人见面相聚,在当时看来很一般,几十年后再看,却令人感慨万千,鲤鱼江的风水好哇,让李青出手大方,1962年的春夏之间接连抛来了两块“敲门砖”,而萧育轩、古华凭这两块砖走进了湖南文学的最高殿堂,并激励和催化他们努力前行,走向更高层次、更宏大文学殿堂的大门。
第二次:《迎冰曲》及《风火录》
萧育轩的《迎冰曲》写于1963年5月,约12000字。
这篇小说写的是,红军出身已到退休年龄的供电所所长鲁炳炎,在一个北风怒吼、大雪纷飞的日子,服从组织决定向新任所长交接班的一段经历。尽管老所长不情愿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山区供电所,但还是极其庄严地交下接力棒。
小说通过描写老所长带领新所长巡视线路和这一过程中所遇冰封雪压的种种非常事件及其处理方式,塑造了老红军鲁炳炎赤胆忠心、胸怀远大、老当益壮、一心为公、艰苦奋斗、关心部下、体贴老百姓、永葆本色的共产党人光辉形象,诠释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主题。
这篇小说1964年3月在《人民文学》头条发表后,全国许多报刊发表评论。著名作家周立波在《文艺报》发文推荐。一些向全国发行的报刊、省级报刊发表评论,《湖南日报》发表知名作家康濯写的评论,《湖南文学》开辟“专栏”发表了韩罕明等多位老作家写的评论。记者、编辑和电影导演纷纷来电厂采访、组稿或洽谈改编等事宜。搞得厂党委书记一时难以适应:“哼,老子革命几十年,也没这小子名气大!”
这篇小说被译成英文,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萧育轩也因此出席1965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其实,这篇小说起初没有投给北京。萧育轩写完小说后,自己虽然感觉良好,很是得意,但心里还是胆怯,觉得《人民文学》是中国文坛的顶级刊物,自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要在那上面露脸发文章,难于上青天。于是,他把稿子投寄给上海的刊物,十几天后,原件被退回;他心里不甘,换了个信封,投寄给广州的刊物,又是原件退回;心里仍然不甘,又换了信封,投寄给本省的刊物。在第三次收到退稿时,他气到极点,难道真的是暴殄天物?突然间,他决定赌一把试试。上午接到退稿,下午就换了信封投寄北京《人民文学》,并在信封上注明:这是多家刊物退回来的稿子,不能采用也是情理之中。
没想到《人民文学》慧眼识珠,头条刊发。萧育轩惊而发愣,哑然失笑,天假几家编辑打瞌睡,才使竖子成名。
1963年,在小说《迎冰曲》手稿漫游沪、粤、湘那段日子,萧育轩还写成另一篇约11000字的小说《风火录》。小说以老电厂锅炉车间两次设备更新事件为背景,讲述了锅炉车间元老魏长青和张德明两段五味杂陈的人生经历。
这篇小说展现了我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发愤图强,敢于同鄙视中国人、对中国搞技术封锁的洋博士史密斯较真较劲;也彰显了工人阶级不安于现状,努力掌握先进技术、尖端科学,要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和人类进步事业有所作为、多做贡献的崇高境界。
《风火录》1965年5月在《人民文学》刊登后,旋即由胡书锷、向彬人、唐建平、郑世俊改编为五幕话剧《电闪雷鸣》,湖南话剧团率先排演后,全国好些省市的话剧团、文工团也排演了这部剧。
如今网上还可搜索到当年北京市二七剧场的前排入场请柬:
定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晚七时十五分在二七剧场由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的湖南话剧团演出5幕话剧《电闪雷鸣》。
敬请光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国戏曲家协会
北京市文化局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三次:《心声》及续篇
特殊年代结束后,短篇小说怎么写?1977年4月《人民文学》刊发的萧育轩的《心声》开了先河。
这年4月6日,萧育轩从北京给我等几位文友的信中写道:
原本打算今年要休息一年,过过痛快的日子,因为账欠得很多,需要宅门不出,才能解决问题,谁知刚过完春节,《人民文学》编辑部通知召开小说座谈会,加上北京好久没来了,有点想来看看。党委见是北京的信,又是开会,也就同意我来,如果是《湘江文艺》,那他们不会同意的,于是就来了。
来了后才知,名为座谈,实则坐而不谈,坐而就写。先后来了几位同志,大都改完稿子就走了,如上海的胡万春等,要来的人也有的因各种原因没有来。现在只有贵州一个同志和我了。小说创作如何写揭批“四人帮”?来京写稿的人都希望编辑部的人讲讲形势,作个报告,而他们说,谁也不能作,各自先写稿子,编辑看了稿子提意见。其他人都带了稿子,而我是两手空空,后来还是改写了那篇旧作《心声》,我记得这篇东西你们都看到过,垂辉也叫过好,月红还给我抄过。由于编辑部等着发稿,所以日干夜干了几天,重写了一稿,他们一看说可以,马上就发排。这篇稿子二万七千多字,我自己觉得写了几个我喜欢的人物,又正是现在需要的,编辑部的同志较为满意。只是可惜急着发稿,没能来得及再详细推敲一下。前天我看了清样,文字还较粗,可是没办法,出来后一定要请你们看一看,是不是我还可以写下去。几年没弄了,写起来很吃力。
《心声》弄完后,他们还要我写续篇,商量后定下写《喜悦》和《进击》,现在《喜悦》已弄完,他们初步肯定,还要丰富一下,弄一遍,这篇也两万多字,有些场景自己还喜欢。问题是来京一个多月了,我想回家,这里生活太昂贵,要花两元钱一天。可是他们想我全部写完后再回去,我正在争取中……
《心声》公开发表后,受到全国文学界的好评,在党政干部中也有强烈的反响,华东区有位省委书记召开常委会会议,就念小说《心声》。这篇小说迅疾被译成英文,引起了国际文学界注目。新华社《参考消息》,转发了外国媒体评论这篇小说的新闻。两个月后,续篇《喜悦》改名为《希望》,在6月号《人民文学》发表。
《心声》及续篇一组三篇,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连,讲述某电厂1976年以后发生的事。作者不仅塑造了梅雪玉这个堪称当时文学界中最早出现的奋起抵制并反对那些高喊“文化革命”口号、篡党夺权阴谋家野心家的中层老干部的典型形象,还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新人的群像,其中如梅雪玉的父亲、老红军梅正楚,以及青工厉志良和老工人周师傅等便是突出代表。他们都立场坚定而顽强,但又各有特色。梅正楚八十高龄仍倔强开朗,赤胆忠心外露;厉志良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苦钻技术,而政治上又是忠心一片,智慧无穷;周师傅也是默默无闻,但肝胆照人,无私无畏。这些英雄形象有的虽着墨不多,却也能使人感染,念念不忘。武震东是个有特色的老干部,他出身、历史、斗争经验都无可指责,却被对手林副书记搞得工作上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不安于养病又不得不去养病,有苦难言,愁肠百结,心灰意冷,但关键时刻幡然觉悟,斗争烈火闪发,领导才华横溢,智慧涌流而出,协助梅书记给了阴谋篡夺电厂大权、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野心家当头闷棍,参与组织和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进击,其性格色彩给人印象深刻。
1977年10月,张光年主持下的《人民文学》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只邀请了20多位作家,有沙汀、刘白羽、周立波、马峰、王愿坚、李准、茹志鹃、邹志安、叶文玲、萧育轩等。当时作协尚未恢复,茅盾应邀以原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名义在会上作了题为《老兵的希望》的讲话,这也是茅盾在特殊年代结束后,第一次出席文学界的会议。会议规模虽然不大,却是转折年代重建文学制度的重要一步。
1977年11月6日,萧育轩从西安写信给陈第雄等郴州文友,分享出席短篇小说座谈会的喜讯。他说,参加这样的会议,聆听老作家们的经验交流,确实受益匪浅。会议着重讨论了生活与创作的问题,提倡从生活出发……
1977年末,萧育轩把《心声》的续篇二《进击》作了认真修改后于1978年初向《人民文学》交了卷。
1978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为萧育轩出版短篇小说集《迎冰曲》。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全国文学报刊园地一度荒芜,萧育轩的这部短篇小说集总共只有12篇作品,除前面6篇外,还有1970年12月写的《火花》、1971年5月写的《铁臂传》、1972年4月写的《向阳峰》、1973年5月写的《扬鞭跃马》、1978年2月写的《抢春人》等作品,各有鲜明特色。
应出版社邀请,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为这本集子写了洋洋一万五千言的评论:《迎冰斗雪报春来——读短篇小说集〈迎冰曲〉》,从多层面、多角度对小说集思想和艺术成就方面的共性和特性,作了精彩严谨的评析。这位有名望的老作家对萧育轩其人及作品作了多个“之一”的概括:总的来说,萧育轩这12篇作品中尽管有的方面,以及有几篇比较起来显得力量稍弱,但小说集中最好的篇章却是宛如斗雪迎冰的战歌,恰似俏也不争春、只报春来到的乐曲。这位工人作者的确可以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短篇小说作家中比较杰出的一个,是这段时期内新出现且成长较快的优秀作者之一。
1980年以后,萧育轩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客从西方来》,其中萧育轩自己比较得意、社会反响强烈的有《孟广德那老头》和《烛泪》。
《孟广德那老头》通过讲述电厂修配车间电焊工孟广德生活工作中一个个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展现了孟老头与周围人的关系以及性格特点。《人民文学》1982年第4期头条刊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为广播剧向全国播发;还有美术工作者改编成连环画。
《烛泪》在1982年由《少年文艺》刊载,1983年获少年文艺优秀作品奖。《少年文艺》创刊于1953年,由宋庆龄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是新中国第一本少年文学月刊。《烛泪》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我没有读过这篇小说,好不容易才从一篇评述萧育轩小说的情节紧张性与变幻性的文章中得到这么一句话:“《烛泪》中的孟教授怀着失望的心情,正准备离开某省时,突然,一个盲人和一个褴褛少年闯了进来,坚持要考少年班。”评论写的这一句,是解释萧育轩小说的情节紧张性,源于“悬念”的精心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