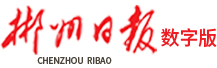□ 李向明
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以其千古不朽的道德文章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他为官以江山社稷为己任,忧国忧民,因直言进谏犯上,两度遭贬南迁。韩愈一生六过郴州,与郴州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在湖南寓居7个多月,创作诗文30余篇,其中一半多的时间在郴州、一半多的诗文在郴州创作,省内唯一的韩愈题刻手迹也在郴州,为郴州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下岭南,六过郴州
郴州的骑田岭古道,连接着长江和珠江水系,是中原通往岭南的陆路捷径,唐代仕宦往来多取此道。韩愈三次穿越南岭,走的正是这条驿道。
韩愈幼时父母双亡,由兄嫂抚养。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四五月间,年仅九岁的韩愈随被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刺史的二哥韩会南迁。两三千里的行程,必须在一个半月内赶到。两年后,42岁的韩会在韶州病逝,韩愈随二嫂郑氏扶柩北归河南老家。这是韩愈第一次往返郴州,虽尚年幼,但对旅途的艰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复志赋》中写道:“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洲庭之漫漫。”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以四门博士任监察御史,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因关中饥荒,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求罢免宫市、宽免百姓税赋,触犯权贵,触怒皇帝。35岁的韩愈与同事张署分别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省)令和郴州临武令。是年腊月,他们冒着风雪离开长安,次年初春方到达任所。两年后,德宗驾崩,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与张署被诏至郴州待命。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韩愈升至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唐宪宗命宦官从凤翔府法门寺真身塔中将所谓的释迦文佛一节指骨迎至宫廷供奉,并送往各寺庙供官民敬香礼拜。韩愈毅然上书《论佛骨表》谏阻宪宗,指出信佛对国家无益,劳民伤财,且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触怒宪宗,差点被处死,幸经裴度等人说情,贬为潮州刺史,责求即日上道。51岁的韩愈第五次过郴州。同年十月,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这次赴任,他走的是从郴州往东经虔州(今赣州)古道。郴地流传一则“韩文公走马”的故事,传说他骑马出城,在坳上乡的一处山坡上,马失前蹄将他摔下马背,马也惊跑了。当地民众得知他是为民请命的韩侍郎,帮他找回马匹,扶他上马,还热情地送上一程。后来,那座山被称为“走马岭”,作为地名沿用至今。
逗留临武,佳话长传
与韩愈一同被贬官的张署也是监察御史,两人政见相同,交情甚笃,此次就职又是一路同行,相互宽慰鼓励。
相传他们来到临武后,张署想留韩愈小住几日,一来休息一下消除旅途劳顿,二来可以商谈今后的打算。韩愈也正有此意,便在临武县城住了下来。两人一边商谈,一边得空游览周边胜景,吟诗唱和。
十来天后,韩愈启程继续往南去连州阳山,张署一路送到与广东交界的九泽水村。他们在这里借宿,次日清晨才挥手告别,各自上路,并约定下次在这里聚会的时间。韩愈在《祭河南张员外文》中写道:“君止于县,我又南逾;把盏相饮,后期有无。期宿界上,一夕相语;自别几时,遽变寒暑。”人们遂把这个村改名为“期宿村”。
到了约定的日子,韩愈骑驴向北,张署坐马向南,两人又在九泽水会面了。他们把马和驴拴在村民的牛棚栏杆上,两人叙旧话新,把酒言欢,不觉已至深夜。正说话时,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吹灭,随着窗外一声虎啸,马嘶驴叫,两人一时不明就里。
村民们知道,这是老虎进村了。他们点起火把,手持刀叉棍棒,纷纷出动,分头寻找马和驴。结果,马找回来了,驴被虎叼走,只留下一滩血污。张署深感惋惜,韩愈却连声大笑:“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众人听得莫名其妙。韩愈说:“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今日失驴,回不了阳山,岂不是预示着该回长安了吗?来年正月就是寅(虎)月,虎来有好兆头啊!”
果然,第二年正月新皇帝登基,韩愈与张署不久后奉诏北归,分别改任江陵(今湖北荆州)法曹参军和功曹参军。虽未回到长安,但毕竟是近了很多。
韩愈在临武作诗《题张十一署官舍》三首。九泽水送别时,张署作七律《赠韩退之》,韩愈到阳山后作《答张十一》回赠。为纪念韩愈和张署在临武登山吟诗,人们把他们登临的官山改名为韩张山。山上建有韩张亭,近年修建了韩张公园。
待命郴城,北湖叉鱼
唐顺宗继位不久,即大赦天下。大约在初夏之际,赦书先后传到张署和韩愈手中,将他们诏至郴州待命。自阳山赴郴,韩愈这次没有北上经临武,而是由湟水(今连江)乘舟东南行,再溯溱水(今武水、北江)北上。碰巧的是,在郴宜骡马古道上与张署不期而遇,两人一同抵达郴州。
郴州刺史李伯康盛情接待了他们,给他们安排专门的住处。因迟迟不见具体的任命诏令,且传闻朝中斗争激烈,两人也只好安心在郴州待命,开始了一段为期四五个月之久的寓郴生活。八月初,唐宪宗即位,再次大赦,韩愈和张署分别被委任为江陵法曹参军和功曹参军。八月中旬接到新的诏书,九月初才离郴赴任。
韩张二人堪称难兄难弟,有太多相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话题,境况的改变解除了他们的精神压力,李伯康也常陪他们游览山水胜迹,彼此酬唱频频。韩愈在郴州广泛接触社会各个层面,参与社会活动,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与刺史李伯康、道士廖法正、青年学人孟琯更是结下深厚友谊。那年郴州遭旱,他随李刺史去女郎庙求雨,应邀写下《代李员外女郎庙祈雨》诗,又作赠诗《李员外寄纸笔》。韩愈离郴不久,尚在赴任的路上就听到李伯康去世的消息,沉痛写下《祭郴州李使君文》。
那年中秋夜,李伯康专门在北湖修筑草亭和玉雪桥,为韩张安排了独具郴州地域特色的“赏月叉鱼”夜宴,一起欣赏北湖水月美景,饮酒赋诗,纾解排遣,也算是为他们即将履新临别送行。韩愈诗兴大发,欣然吟出七言古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写尽了贬谪蛮荒的辛酸经历,抒发了两人不能回京而只能去江陵的无奈和感叹。该诗后来收入《唐诗三百首》。接着又作了一首五言排律诗《叉鱼招张功曹》,诗句优美,绘声绘色地再现了在郴州北湖月下叉鱼的情景,触景生情地道出了遭谗蒙冤的身世噩梦和隐衷伤感。后人为纪念韩愈,曾在州学和北湖先后建有景贤祠,在北湖小岛上建立叉鱼亭,塑造韩愈铜像,竖立“叉鱼”诗碑,成为一处彰显郴州深厚历史文化的独特景观。
韩愈对郴州山川形胜、地灵人杰的地域风物情有独钟。当年苏仙岭景星观有个廖道士,名法正,曾学于衡山。韩愈作《送廖道士序》赞其“气专而容寂,多艺而善游”,精准描绘郴州一带“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中州清淑之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并预言“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据《湖广通志》等书记载,唐懿宗曾召廖道士入宫行道斗法,被敕封为“元妙真人”。他受事不受官,事毕回郴修道,后在连州靖福山白日升仙而去,成为郴州“九仙二佛”之一。其仙山廖仙岭在郴城西,景星观今存韩愈《送廖道士序》碑刻。
韩愈发现郴州青年孟琯勤奋好学,非常器重他的才华,决心培养、举荐这个青年。特为之作《送孟秀才序》,称他“年甚少,礼甚度,手其文一编甚钜”。孟琯果然不负韩愈厚望,元和五年(810)一举金榜题名,成为郴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官长安县令,著有《岭南异物志》《南海异事》数卷。
韩愈在郴州还得过一场疟疾,他的《谴虐鬼》诗对郴人治疗疟疾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诗人巧借古代神话和楚辞中的丰富意象,将疟毒拟人化,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积极乐观的抗疟情绪和人神和谐共处的意愿。同时,也记录了弥足珍贵的郴地民俗文化和抗疟史料。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此诗选入高考语文模拟试题。
泛舟便江,昌黎经此
便江为湘江支流耒水中游永兴县境河段,是中原与岭南交通的黄金水道。古人南下渡长江,乘舟船过洞庭,经湘江入耒水,由便江至郴江,自郴州经湘粤古道进入岭南地区。据查考,唐宋之际贬谪到郴州和岭南的官员数百人,著名的如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柳宗元、秦少游、寇准、苏东坡等,他们南来北往多取此道。韩愈六过郴州,五次经过便江。
便江丹霞碧水,人文荟萃,似漓江,如武夷,拥有精巧的蜂窝岩、狭长的一线天、众多的丹霞窾洞等独特景观。韩张同赴江陵就职,之前过便江只顾匆匆赶路,无心赏景,这次时值秋高气爽,又逢遇赦,难得的好心情。泛舟便江,韩愈诗兴大发,连吟三首。在《湘中酬张十一功曹》其二中写道:“山作剑攒江泻镜,扁舟斗转急于飞。回头笑向张功子,终日思归此日归。”远看山峰突兀状如剑聚,近看江水清明状如镜移,将便江的奇秀山水和诗人的愉快心情写得生动传神,情景交融。
舟过一石窾时,他们兴致勃勃地登岸探幽。窾洞位于便江北岸,时称北岩,上覆下空如石屋,窾底连江,内有石廊,石壁如削。见石壁上有前任郴州刺史李吉甫两年前题写的手迹,所言“蒙恩除替,归赴京阙”等,又有南朝梁的题刻,字迹漫漶,韩愈乘兴以白垩(白土)题写“昌黎经此”四个遒劲大字。后来,不断有人慕名到此游历,留题石刻。韩愈的手迹也被清道光年间永兴知县王晋庆“命工镌于左”,刻成一阳一阴两方石刻,字径尺五见方,阴幅如帛,阳幅似锦,交相辉映。为纪念韩愈泊舟留题,这个石窾遂更名“侍郎窾”,江心的沙洲被称为“文公滩”。明代兵部郎中李永敷《侍郎窾》诗曰:“昌黎闻说此经过”“窾号侍郎终不朽”。
2005年,侍郎坦摩崖石刻群被重新发现,经湖南省文物局专家认定,现存题刻17方,其中唐代题刻11方,除韩愈和李吉甫外,还有柳宗元、杨於陵、杨景復、安政恒、韩泰、宋柷、梁褒先、曹琰等人,他们都是重臣名流。这是湖南省首次发现南北朝时期的摩崖石刻、首次发现的唐代石刻群、首次发现的韩愈手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2013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