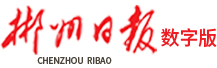□ 欧阳朔
正月初一,我携妻女回老家拜年。路过一片松树林,我指着那些高大的松树对女儿说:“这是我们家的树……”她说:“不可能吧?你都离开家乡几十年了。”我说:“分山时,算了我的人头。我参加工作后,这个山林权没有调整。你说有没有我的份?”看她将信将疑的样子,我感到些许沮丧和难过。哎,她是城里长大的,哪能体会到那山那树就是我的幼儿园呢?
我老家是丘陵地貌,四条小山脉上,长着三大片松树林。后龙山一大片,被山沟隔成六小片,每个生产队各占一个山岗,有上万棵马尾松,当地人叫枞树,大者如桶,小者合围,遮天蔽日,蓊郁茂密,是老家世代守护的风景林。牛牯坪和席子岭各有一片。这里路更远,地更平,树略小,地上盖着枞毛,枞毛上躺着松塔,松鼠跳来跳去……我们经常在这里捡柴火、玩滑板、捡蘑菇、摘地菍。对我们来说,这三片树林既是劳作场所,也是童年的乐园。
第一次爬树,我是在后龙山学会的。屁股上插一根长棍,抱住树干,脚踩树丫或树皮,肚子一鼓一缩,往上攀登,爬上树冠后,低头一看地上,哎呀,人在半空中,离地比房子还高啦。树梢之上,南风一吹,树梢就会摇摆。松涛随之而来,呼啸着,把绿涛一波一波传上远方。这时候,脑壳就会发晕,辨不清东西南北;勇气也吓跑了,头发直竖,恨不得向谁呼救。大树会不会折断?天地会不会翻转?谁也救不了谁!我闭上眼睛,暗暗给自己打气——不要怕,怕也没用,谁来救你!还好,适应一阵子,就不怕了。取出长杆,哗啦哗啦,把松塔打了下来。有人说上树容易下树难,开始我不懂,后来才明白,下树时看不清落脚点,只能用一只脚去试探虚实,一只脚踏实了,才能换条腿走下一步。踏空了,或者踩到枯丫了,都有可能造成闪失。
七八月酷暑,正是地菍成熟的季节。松林里,地菍很多,一长片一大片,五六月开花,七八月结果,翠绿打底,点缀着果实,像铺了一层地锦。地菍熟透了,是紫黑色的,拇指那么大,圆嘟嘟的,吃在嘴里沙沙响,甜丝丝的,如同天赐山珍。捡柴也好,割草也罢,干活间隙,我们都会挑选一些又大又熟的地菍,就着山泉洗一洗,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吃个痛快,再灌几捧清泉,然后才挑着担子回家。父母一看我白牙染成了黑牙,晓得我吃过地菍了,也就不急着煮饭菜了。饥荒岁月,地菍不顶饿,关键是易得,免费,有甜味。
松树林里,还有很多山珍,比如枞毛糖和野菌。我只见过一次枞毛糖。那是秋冬之际,一夜之间,牛牯坪的枞毛突然裹上了白色糖晶,白茫茫一大片,像下了一场大雪,又像漫天里洒了石灰。摘下小树枝,用舌头舔一舔,嗨,真好吃,是甜的!还带有松香味!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是松树的分泌物,并非传说中的野蜜糖。至于拨开枞毛采蘑菇,那是春天如约而至的喜悦,白色的,褐色的,绿色的,五颜六色,遍地都是。雨后天晴,根本采不完。至今我还记得母亲教我的一条经验:“越是漂亮的菌子,越要小心中毒,千万不要被她给迷惑了!”想一想,识人和找菌不是同理吗?
老家也有很多动物,现在比过去更多。我见过冬茅老鼠、蜜蜂窝、野猪、麂子和各种各样的鸟。记得有一年,也是正月初一,薄雪初晴,我独自来到牛牯坪散步,刚走入林中,就听见鸟儿啼啭啁哳,像极了百鸟朝凤。举目四顾,却不见一丝鸟儿踪迹。我轻抬脚步,靠近去倾听,鸟儿们好像发现了我,竟然玩起了集体静默。折转身子,才走了几步远,她们又啾啾唧唧,唱起歌来了。回家后,我问三哥:“怎么突然间多了很多小鸟?”他说:“这不奇怪啊。不砍柴了,不烧山了,鸟儿就多了,野猪也多了。”
说到童年趣事,我想起了父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村里分田分土分山林,我家也分到了一百多棵松树。母亲问他:“人家都在砍树,我们也砍了吧?”父亲说:“不能砍,这是风景林。”母亲说:“要是上面政策变了,队里反悔了,又要收回山林,怎么办?”父亲说:“也不砍。那就给村里留点树种。”结果,牛牯坪被人剃了个光头,唯独我家留下了那一百多棵松树。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古树仍然矗立在半山腰。由于干旱、虫害、盗伐,现在只剩下一小半了。所幸松树繁殖能力强,现在又长了很多小树。每次路过这片松林,我都要停下车子,站在路边,喝一口水,引颈遥望,发一阵呆。妻子从不催我赶路,她知道我在想什么。那山,那树,那人,我和她说过好多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