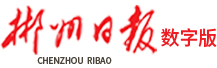□ 陈建凯
今天这个日子特别,是母亲的忌日。我们兄妹围在褪了色的相框前,一声声唤着“妈妈”。可母亲只是微笑,饭菜递到跟前也不接,只有那双眼睛,温柔地看着我们。
三十多个春秋翻过去,多少事都淡了。偏是母亲走的那天,痛像扎进心口的刺,年头越久扎得越深。
20世纪80年代某个冷雨黄昏,母亲在兴宁镇东门口公厕解手时突然倒下,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没了气息。急救室的白炽灯明晃晃照着,我们兄妹跪在冰凉的水磨石地上,眼睁睁看着白布蒙住母亲温热的脸,天当真塌了。那时,我们兄妹都不到30岁,真是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幸福哪里找?
那些年,命运的齿轮有时是这样的无奈。我们家本是干部家庭,父亲却因特殊缘由工资被停发,全家七口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撑着,生活陷入困境。早晚两顿稀粥,晌午才见得到米饭,红锅烧出来的菜在粗瓷碗里泛着寡淡的光。就是这样的菜,我们的筷子伸过去,也得掂量着夹。
父亲本就郁闷,平日里依赖的烟、酒又没了着落,心情便愈发消沉,时不时冒出不想活了的念头。
那时,大家都没有吸烟不利健康的意识。为给父亲解闷,母亲要我兄弟俩去商店、会场、路上,捡纸烟屁股(那时纸烟没有过滤嘴)。晚上,两个妹妹,负责撕烟屁股纸,母亲教我和哥哥用自做的木匣子卷烟。日子久了,两个妹妹踩在板凳上,竟也卷得有模有样。
那年大雪天,我和哥哥钻进会场,挎包装满时撞见个酒鬼。他踩着我的手背抢挎包,用巴掌把哥哥的半边脸抽出了五个手指印。回到家,母亲掀开棉袄,把我肿得像馒头的手揣进怀里,滚烫的泪珠子,像春雨一样,啪嗒啪嗒砸在我发旋上,也洇湿了我满是补丁的衣角。
我们回老家,要走四十多公里路,中间还要翻几座大山。记得有一年春节,父亲背着大妹走得踉跄,母亲驮着小妹直打晃。迎着山风,母亲喘喘粗气,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讲述《三打白骨精》,汗珠子顺着鬓角,在山路的青石板上,砸出深色的花。
母亲说,她这辈子最揪心的事,是1967年把我和哥哥送进深山学堂读寄宿,把两个妹妹寄养在乡下亲戚家。
每到周末,学校师生都回家了,只有我和哥哥,像屋檐下孤单的雏燕,抻着脖子等母亲送腌菜来(一瓶子菜吃一个星期)。
接妹妹那天,母亲看着差点认不出、缩在灶灰里,像只又脏又瘦猫崽的小妹,把人儿搂在怀里,摸了又摸,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半天,愣是没掉下一滴来,也没说一句话。
东门口公厕那扇木门,成了我心头永远的伤疤。明知母亲的病未好透,我还奔着所谓前程离开。那天傍晚您独自走向生命的终点时,可曾回头望过我们熟睡的窗户?
清明雨又落,纸灰化作黑蝶。母亲,您走后这些年,我们兄妹活成了您盼望的模样。只是饭桌上永远少副碗筷,您手把手教的卷烟手艺失了传。唯有思念,在年节里愈酿愈浓,稠得化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