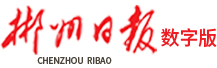□ 陈小会
打开汝城理学古镇的正确方式,是品读上黄门。
上黄门,宛如一朵莲花的茎,纤细而坚韧,串联起古镇的往昔与今朝。
窄窄的古巷,青石板泛着幽光,两侧店面鳞次栉比,茶香混着市井的烟火气在檐角流转。我常坐在荷静阁茶楼临窗的位置,看阳光斜斜地切过雕花窗棂,在桌面上织就一方金莲。那天,店主胡巧莲用当地杉树园莲花岩产的“汝莲”泡了一壶绿茶,让我品尝。她说,这款茶叶,细闻慢品,有着莲的清香。吸着带莲香的氤氲之气,那些关于莲的传说,便在袅袅茶烟中次第绽放。
濂溪祠的莲子
公元1050年—1054年,周敦颐任桂阳(今汝城)县令,勤民耕读,风节慈爱,吏治彰著。周子爱莲,在官署前的池塘里种满莲花,民间也广种莲花,莲香自此飘荡汝城。他更有着莲的品格,可谓:一颗莲心,一世廉性。周敦颐的思想之深远博大,离不开学问上的钻研开拓,因而成为理学鼻祖,但更离不开他刻在骨子里的清廉与刚正,成为文人士大夫心中的“莲范”。周子的《爱莲说》,为莲赋予了高洁的灵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的形象自此深入人心。黄庭坚曾评价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而“光风霁月”被历代文人们认为是对君子人格最贴切的评价。
公元1220年,为纪念周敦颐,时任汝城县令周思诚建濂溪祠,祠内的希濂堂前,一池莲香,满院清气。周子在汝城播下的莲籽,千百年来,早已长成“亭亭净植”,尔后,形成的莲文化,早已清香四溢。莲文化因而在汝城有着深厚的根基,它与廉、怜同音,恰似一把精巧的钥匙,开启了一段段尘封的人文佳话。
新井村的莲心
朱余周的故事,是古镇最苦涩的莲心。十五岁那年,叔父婶婶相继离世,留下襁褓中的堂弟云伯。她剪断了自己的红装梦,在晨曦未启时耕作,在月光浸窗时纺织,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屋旁的姑婆井,是她亲手挖掘的清泉,不论旱涝,始终盈盈如眸。传说她为排遣长夜寂寞,每晚熄灯后撒百枚铜钱于地,摸黑一枚枚寻回,数十年如一日。这看似笨拙的坚持,何尝不是一朵莲花在淤泥中倔强挺立的姿态?
后来云伯成家立业,她又为侄辈操持家业,直到八十五岁离世。乡人将她的神主供在祠堂主位,把那口井砌成双井,唤作义井。明朝御史范辂上奏朝廷,皇帝封她“靖一”谥号,牌坊上的石纹至今还刻着她的故事。如今井头村的老人们说起她,仍尊称一声“义井姑婆”,仿佛这个称谓里藏着千年不灭的烛火,照亮了古镇最深处的善意。
绣衣坊的莲骨
范辂的故事,是古镇最刚直的莲骨。正德年间,他以监察御史之职巡视江西,面对宁王朱宸濠的跋扈,他挺直腰杆上奏弹劾,宁愿入狱也不折节。被贬龙州的路上,刺客的刀光在黄茅港的夜浪中湮灭,他却在颠簸的船舱里写下“此心若有纤毫伪,口舌漂零不得还”的誓言。三十载为官,家无长物,唯有俸银九十两,布衣木笏,守着祖上的薄田。
益道村的绣衣坊至今矗立,那是朝廷为旌表他的廉洁而建。祠堂里的木刻传记,记载着他拒收纯化王谢金的往事,“空囊果称珠玑富”的诗句,在岁月中愈发铮然有声。范辂的石像立在中丞公祠前,目光如炬,仿佛仍在凝视着古镇的晨昏,守护着莲的清白。
始生堂的莲魂
鹿宾的故事,是古镇最温柔的莲魂。当他看到寿江边漂浮的女婴,毅然立下“乾坤合德碑”,以阴阳相生之道劝禁溺女。他建育婴堂,置义田,用租银补贴贫困人家,让那些本应凋零的生命得以绽放。百姓称他的育婴堂为“始生堂”,因为每一个存活的女婴,都是他用仁心重新赋予的生命。
文塔旁的君子亭里,他写下《君子亭铭》:“所愿君子,千秋共盟,厥守坦坦,厥守硁硁。”这不仅是他的自勉,更是古镇精神的写照。如今寿江的水依旧流淌,岸边的石碑虽已斑驳,却永远刻着一个官员对生命的敬畏,悲天悯人,如同莲花呵护着每一滴露水。
暮色中的理学古镇,青瓦上飘着炊烟,宛如莲瓣上凝结的晨露。周敦颐的《爱莲说》在祠堂的飞檐间回响,而朱余周的坚韧、范辂的清廉、鹿宾的悲悯,早已化作古镇的血脉,让每一块青石板都浸润着莲的品格。
当我再次走过上黄门,忽然明白,这个叫莲的地方,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所在,而是无数颗像莲花般洁净的心,在时光长河中绽放的永恒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