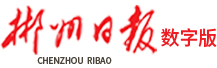□ 陈华英
当代热门女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诗意笔触描绘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现代文明对原始生态的侵蚀,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失落、生态危机、精神困境的深刻叩问。该书自出版以来,在文坛影响深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发行全球,成为青少年理解多元文化的经典读物,更以全票斩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好作品百读不厌。再次捧起这本书,恍若与故人重逢。书页间浮动着大兴安岭松针的清香、驯鹿奶的醇厚,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温热——那是文字在呼吸,是字符在跳动。迟子建以滚烫的真情让那些即将湮没于时光的人与事,在字里行间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字里行间的生命温度
这部作品的主题重大而深刻。面对如此厚重的命题,迟子建没有振臂高呼,也没有厉声质问,而是轻展笔墨,让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我”,坐在希楞柱里,以额尔古纳河般平缓的语调,将百年沧桑化作耳畔絮语——那些字句裹挟着林间的晨露与篝火的余温,看似平淡,却每一个字符都带着生命的脉动。
这份温度,融于鄂温克人琐碎的日常里。“我”回忆儿时的情景:男人们踏雪进山打猎,女人们在家缝兽皮、熏肉干、挤驯鹿奶,孩子们追蝴蝶、采野果、捡蘑菇。每逢喜事,营地燃起篝火,人们手拉手跳斡日切舞:女人在内圈向右转,男人在外圈向左转,这一左一右地旋转,使那团火也仿佛跟着团团转起来。这种朴素的描写还原了生活最本真的质感,让读者触摸到猎民生活的粗糙与温暖。
这份温度,更藏在鄂温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他们从不砍伐活树当烧柴,只烧干枯树枝、被雷电击中或狂风刮倒的树木;连驯鹿都懂得不过度取食,啃几口青草或树叶便离开,让草木依旧繁茂。“我”和拉吉达发现四只未睁眼的水狗幼崽,便满心欢喜地期待母水狗回来,却在母水狗归洞时放过了它——“我想那四只小水狗还没见过妈妈,若睁眼只看到山峦、河流和猎人,一定会伤心的。”
而最动人的,是人与人之间流淌的温情。伊万倾尽所有买下被逼为妓的俄国女孩娜杰什卡,将她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杰芙琳娜成为新娘的当天就被抛弃。在她走投无路时,达西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娶了她。在她遭婆婆打骂时,他以自残护其安全。年幼的列娜为了父亲的安全而一夜未睡,终因太困在搬迁途中伏在驯鹿背上睡着而冻死。尼都萨满一个大男人竟用两年时间收集山鸡羽毛,悄悄为心爱的达玛拉缝制了一条百合花形状的裙子。达玛拉捧着那条裙子,说这是她见过的世上最漂亮的裙子。
这些带着生命温度的片段,恰似大兴安岭夜空中缀满的星星,照亮了鄂温克人林海中迁徙的漫漫长路,也暖透了读者的心。
文字生长的养分根基
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如此温暖人心,正因为作者倾注了无数汗水与精力——那些文字像吸足了晨露的草木,变得丰盈饱满,处处透着蓬勃的生命力。
迟子建在该部作品的跋中写道,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需要种子、泥土,还有阳光的照拂、雨露的滋润以及清风的抚慰。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种子”,源于迟子建对鄂温克族的关注。2003年,她得知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消息,目睹这个民族文化的消逝与生活的困境,心中涌起难以言说的忧郁与苍凉,便着手收集资料,等待创作的契机。不久后,朋友寄来一篇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命运的文章:柳芭带着绚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却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归森林,终在困惑中葬身河流。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她,让她预感到,一条艰难而又自然的回归之路,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时机成熟后,她实地探访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情况,找到了一粒沉甸甸的“种子”。
诗人艾青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额尔古纳河右岸》生长的“泥土”,是大兴安岭地区的土地。这片辽阔而苍茫的林地是故事发生地,也是作者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她出生在漠河北极村,大兴安岭的雪是童年时的游乐场,黑龙江的冰是少年时的玩伴;她熟悉风穿过松林的簌簌声,知道雪落在脸上的冰凉。这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让她的文字毫无隔阂,仿佛一个鄂温克人在娓娓讲述自家的往事。
即便如此,她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她用整整三个月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她追随重返深山的猎民足迹,来到他们的猎民点,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看那些觅食归来的驯鹿悠闲地卧在林地上。她跟他们一起品尝醇美的驯鹿奶茶,也被辛辣的口烟呛得跳起来……扎实的采访与调研,让作品扎根的“泥土”愈发厚实而肥沃。
文字的生长同样需要适宜的环境与心境。迟子建虽然定居哈尔滨,却特意将这部作品放在故乡来写。故乡的地气浸润笔端,窗外连绵起伏的积雪山峦映入眼帘,亲人的温情萦绕身旁——这些,都化作了滋养这部作品生长的阳光、雨露、清风、明月。
作者与文字的血脉相融
迟子建的文字之所以能直抵人心,还源于她将生命体验注入文字——她用泪水与热血喂养文字,使每个字符都拥有心跳。
这番生命体验,源于她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迟子建的爱情姗姗来迟。1998年,34岁的她邂逅了师范同学黄世君,并结为伴侣。黄世君时任塔河县委书记。两人志趣相投,生活甜蜜幸福。然而,命运在2002年猝然转折——黄世君因车祸意外离世。这场变故给迟子建带来沉重打击。她将悲痛融入《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通过文字重构生命的意义。
2008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迟子建眼含热泪说:“这部作品里有我爱人的影子,他教会我,疼痛可以被文字温柔地包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过程,正是她用文字完成自我疗愈的过程。
在文中,我更多地看到了作者自身的情感倾诉。
文中有多处对父母美好爱情及幸福两性生活的描述;有多处对“我”两度美好爱情及幸福两性生活的描述;有父亲离世后,孤独的母亲对爱情的再次渴望;有“我”在第一任丈夫离世后,再度遇到爱情时的温暖幸福。
文中达玛拉、“我”身上有很多作者本人的影子。而林克、拉吉达、瓦罗加的形象则凝聚着她对丈夫的追忆。书中林克遭雷击身亡、拉吉达冻死在马背上的情节,实则是她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这些男人外出前,都对自己的女人许下了令人心动的情话。然而,他们却是一去不复返。这与作者夫妇2002年“五一”假期诀别时的情景何其相似。
我忽然明白,好的文字从不是刻意“写”出来的,而是用生命的真情“养”出来的。